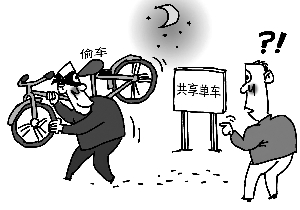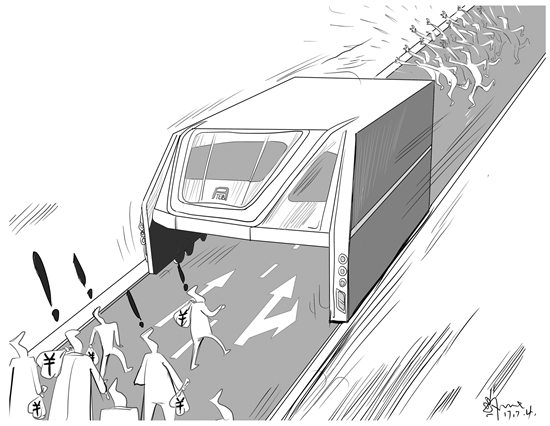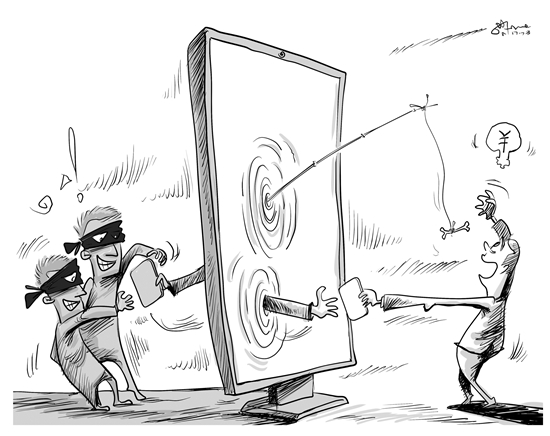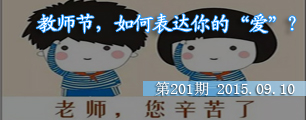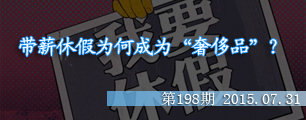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不久前,新加坡一个赌场以欠款为由将我们的一位乒乓名人告上了香港高等法院。事件爆出后,该名人表示欠资事件乃是亲友与赌场的纠纷,自己只是帮忙取筹。一个多月过去了,真相如何,仍需拭目以待。然事件关联到了赌博,确凿无疑。
赌博,是用钱物作注以比输赢的一种娱乐活动。有专业人士研究,赌与博两字连用,是唐宋以后的事,然行其实者历史悠久,光是名堂就五花八门,樗蒲、呼卢、关扑、长行什么的,数不胜数,至于明朝胡应麟所说李清照《打马序》“所举当时搏戏,又有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等等,“今绝不知何状”的就更多了。杨明照先生认为,如樗蒲一类古之博戏,“早已被淘汰,其制其术,无须再为详考也”。不过,了解了解,对认识古人日常生活的侧面也不失为一种趣味。
樗蒲与呼卢是一回事。李肇《国史补》云其玩儿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云云。实际上就是掷骰子,五子全黑的叫“卢”,属头彩。所以掷之时,无不希望能得全黑,加上一般都是且掷且喝,赌博因之又称为“呼卢喝雉”。《晋书·刘毅传》载,刘毅“与刘裕协成大业,而功居其次”,很不服气,“每览史籍,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有次“于东府聚樗蒱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刘毅先掷得雉,很高兴,但嘴上说:“非不能卢,不事此耳。”到刘裕了,“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刘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硬是绝杀了刘毅。当然了,这记载是要坐实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英明。
赌博中还有一种关扑,比较有趣,那是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就是如果看中了某件商品,可以照价付钱,也可以下点儿注来赌,赢了东西拿走,输了把钱留下。宋朝人很爱玩儿关扑。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中一个理由是:“又官吏无状,于给散(青苗钱)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宋刑统》虽然明确“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然对关扑,却是网开一面。《东京梦华录》云:“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届时,举凡“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均可关扑。寒食、冬至时也是这样,“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赵彦卫《云麓漫钞》佐证了《东京梦华录》的说法:“惟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开封府出榜放三日。”赌博嘛,碰运气的成分自然居多。洪迈《夷坚志补八》“李将仕”条云,有持永嘉黄柑过门者,李将仕“呼而扑之,输万钱,愠形于色”,气得他说:“坏了十千,而一柑不得到口。”《能改斋漫录》云,章得象与丁谓两个达官某年寒食节也玩了回关扑,章赢了,“丁翌日封置所负银数百两归公”。第二年寒食节两人又玩儿,这回章输了,丁则马上要钱,章“即出旧物以偿之。而封缄如旧,尘已昏垢”,结果丁“大服其量”。为何服了,不言自明。
赌博之危害人所共知,前人早有清晰的认识。“呼卢喝雉连暮夜,击兔代狐穷岁年”(陆游),浪费时间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后果:轻的,“胜贵欢悦,负者沈悴”(马融《樗蒲赋》);重的,“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李肇《国史补》),乃至“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韦昭《博弈论》)。所以,历来有识之士对赌博都嗤之以鼻。葛洪《抱朴子外篇·百里》谈及选官,而“选之者既不为官择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谓不任”时列举了几种情况,“或有秽浊骄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判者矣;或有暗塞退愦,而庶事乱者矣”,接着也说到了“或有围棋樗蒲,而废政务者矣;或有田猎游饮,而忘庶事者矣”。东晋陶侃为官,“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他常跟手下人讲这个道理:“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因此,手下“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樗蒲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在陶侃眼里:“樗蒲者,牧猪奴戏耳!”牧猪奴戏,因此成为对赌博的鄙称。
在今天,对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参与赌博早有各种明文规定。遏制这一不良嗜好,早已超越他们个人的范畴,而是当下干部队伍建设的必须。
| 王石川:不妨晒晒地下赌场牛气何来 2014-01-27 |
| 李光金:世界杯“治赌”需要“治网”思维 2014-06-23 |
| 王石川:警察开设赌场罚金两万太温柔 2014-06-25 |
| 李 斌:“官赌”毒于虎,治理不能停 2014-10-14 |
| 朱永华:网络灰色心态比裸奔女孩更需要救治 2014-10-21 |
| 严 絮:汪峰需上一堂“自黑课” 2015-12-25 |
| 有多少红包接龙暗藏赌博陷阱 2016-06-01 |
| 【图说】飙车还是玩命? 2016-08-16 |
| 冯导“开撕”真是为对赌协议? 2016-11-23 |
| 国乒当从孔令辉事件中记取什么 2017-06-01 |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957号 | 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957号 | 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38) |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1630) | 京ICP备11015995号-1 | 联系我们:zgw@workercn.cn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媒)字第185号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举报电话:010-84151598
Copyright 2008-2022 by www.workercn.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