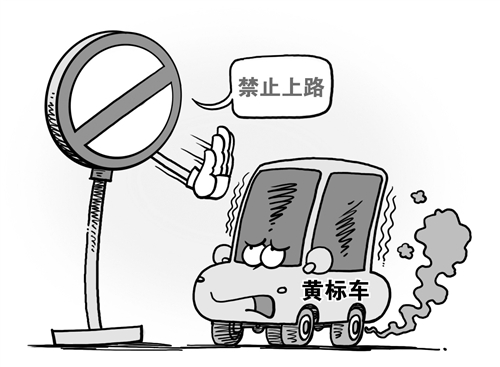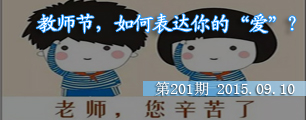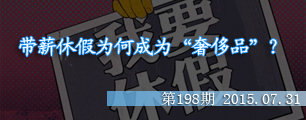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30年前的作者
在环绕着“科班出身”的现实环境下,广播电视大学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和80后、90后不同,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数不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边读书边工作,读的法律院校是广播电视大学,检察院就是实习的课堂。
上个世纪重建后的检察院,人员来自方方面面,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兴起“文化育检”之风,文凭开始“吃香”,老牌大学自然不必说,就连有“工农兵大学”学历的同事,也给人“鹤立鸡群”之感。那时我们正值青春燃烧的年华,渴望读书,因此院里举办了文化补习班,让我们这批知青出身的年轻人都顺利地考入了广播电视大学,这在当时落后的山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我们读书期间,有两个人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一个是我们的主任老许,他是一个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湖北大学法律系的老牌大学生,他的许多同学都是教授和高级记者,这在我们落后的山区是少见的。由于海外关系,他“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法”实施后,始得到重用。在我们院里,老许既是文化带头人,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头儿”,常常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星期六晚上吹着口哨带着我们去看电影……
还有一个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小张,是我们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本来他在省院工作,后来被选派到山区支援基层建设。他的法学理论功底深厚,认法不认人,往往为一个案件据理力争,让一些领导颇感头疼。电大毕业时,我写的一篇《关于如何保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探索》的论文,被评为优良,但小张认为应该评为优秀,专门跑去和论文评审委员会交涉,让论文改为优秀。
读广播电视大学,只能在电视屏幕上与老师见面,收听他们讲课的录音,这之间似乎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让人感到又近又那么遥远。尤其是在考试时听播音试题,让人感到格外紧张,因为手抖动的缘故,以致有些同学把“一”字画成波浪形了。还有些题目没有听清楚,于是就蒙,竟然也蒙对了不少。虽然闹了不少笑话,但后来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读广播电视大学,让我们增长了知识,开了眼界。于是,茶余饭后成为我们学习探讨法学的沙龙。在我们同学当中,有一位同学对刑法学情有独钟,对专家学者崇拜得不得了。那时刑法学界流行“北高南马”的说法,指的是著名刑法学专家高铭暄和马克昌。当有人发表与两位专家不同的看法时,他就会和你争得面红耳赤。他说理有个特点,就是先承认你有些观点,然后驳斥你的是“但是”。我们好多同学,都在他的“但是”面前败下阵来。
我爱好写作,平常喜欢写写画画。有了对法学理论的一知半解,同时也是为了完成调研宣传考核任务,我也试着写一些有关法学理论探讨的文章,但是投稿后总是石沉大海。老许知道后对我说,讲理论,我们说不过大学的学者教授,但是我们在基层,有着司法实践的长处,你不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在老许的指导下,我的一些文章果然破天荒地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
我们的检察长虽然出身“工农干部”,但对我们的学习很重视,不仅在经费中保证我们的学习,也要求我们所在科室负责人在工作安排中要保证我们的学习时间,并有意识地把我们这批学员安排在批捕、起诉以及当时的经济检察等部门锻炼,按照他的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们电大这批学员果然不负众望,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一点也不亚于全日制毕业出来的本科生,后来都成为检察院的骨干,让院里检察业绩焕然一新。年底,院里杀了一口猪,请大家吃年饭。检察长端起一碗苞谷酒说,感谢各位了,说罢一饮而尽。那一刻,我们心头都是热乎乎的。
那时我们以为穿上了检察制服,读了书办了案,就成为了检察人。其实,我们离真正的检察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拿办案来说,老同志用心办案,而我们喜欢只用条文说事。一次老许带我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嫌疑人是一个农民,家庭特别困难,因为孩子想吃肉所以偷了别人的腊肉。从价值数额上看,对照法律条文规定嫌疑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但老许在汇报时建议不捕不诉,理由是犯罪危害性不大,且嫌疑人系偶犯并得到被盗人的谅解。这在当时的“严打”期间是需要勇气的,表现出一个老法律人的责任与担当。那一次我体会到,司法实践才是真正的大课堂,里面有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学员也从青年变为老年,老许、老检察长也离开了我们。但电大的学习生活,却丰富了我们的检察人生,镌刻下了那个时代的标记,让我们久久难忘。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957号 | 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957号 | 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38) |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1630) | 京ICP备11015995号-1 | 联系我们:zgw@workercn.cn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媒)字第185号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举报电话:010-84151598
Copyright 2008-2022 by www.workercn.cn. all rights reserved